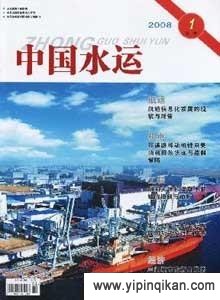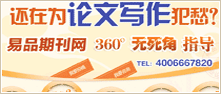澳大利亚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及其启示
澳大利亚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及其启示
【摘要】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是澳大利亚侵权法上休闲体育活动过失致害责任的特殊条款,澳大利亚2002年的侵权法改革对该条款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主要由“危险性娱乐活动”、“重大受伤风险”和“显著风险”这三个重要概念构成。判例法在该条款的具体适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学者对该条款多有争议,但它符合过失责任在休闲型体育中的发展趋势。立法者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在限制过失责任的同时,不影响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关键词】澳大利亚侵权法;危险性娱乐活动;重大受伤风险;显著风险
一、澳大利亚侵权法改革与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产生
20世纪末,澳大利亚法院在过失侵权案件中大多倾向于让受伤者获得充分赔偿,法官对普通法上过失概念的解释越来越宽泛,导致人身伤害诉讼尤其是过失之诉大量增加,损害赔偿额也随之不断攀升,被告及其背后的保险公司因此不堪重负。
2000年前后,一家知名保险公司的破产终于在澳大利亚引发空前的“保险危机”(insurance crisis),保险机构纷纷撤出澳洲市场,第三方责任险的保费大幅上涨,很多组织机构不愿购买责任保险。[1]
但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保险已经深入侵权赔偿体系,责任保险已成为侵权法系统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因此,责任险的缺位严重影响到侵权法赔偿功能的实现,此前一度依赖于保险的损害赔偿体系岌岌可危。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政府认识到应采取措施“通过侵权法的改革来实现平衡”,并迅速成立了一个由数名专家组成的“IPP委员会”,[2]该委员会针对侵权法上过失责任的修改意见形成了著名的“IPP报告”。“ IPP报告”提出了限制过失责任的改革目标。[3]在IPP委员会的推动下,澳大利亚各州政府相继启动改革,重新审视过失侵权法,并以“限制因疏忽或大意造成的过失责任及其损害赔偿额”为目标制订民事责任法。[4]其中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率先制订了2002年《民事责任法》和2003年《民事责任法》,在立法结构和一些特殊性制度(如本文研究的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规定上非常相似,它们成为这次民事责任立法的典范。
在这次改革中,来自休闲体育产业的呼声最高。澳大利亚是一个运动盛行的国度,其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令人瞩目。人们将体育精神践行到日常生活中,澳式足球、橄榄球、滑雪、探险、跳水、打猎等活动非常流行,但与休闲体育如影随行的是高频率的运动伤害。在保险危机前,休闲体育伤害的巨额损害赔偿金主要由致害方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来承担。保险危机爆发后,休闲体育产业受到严重牵连,之前通过责任保险转移风险的道路眼看要被堵死。当时的情况如果继续恶化,不仅可能会使休闲体育产业遭受巨大打击,还可能影响到澳大利亚人以运动为乐的生活方式。因此,“旅游业、户外休闲活动组织、休闲体育组织为推动改革而努力游说,让法律改革的步伐超出了过失侵权法律审议小组所建议的程度”。[5] 2002年《民事责任法》颁布不久,新南威尔士州率先在2002年底通过《民事责任(个人责任)法修订案》(Civil Liability Amendmen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ct 2002),将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写入了2002年《民事责任法》。[6]这也是该条款首次面世。此后,这批制定法历经多次修改。新南威尔士州提供的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范本被各州侵权法所仿效,昆士兰州在随后制定的2003年《民事责任法》中就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二、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构成-以2002年《民事责任法》为分析文本
根据2002年《民事责任法》第1章第5(F)、 5(K)和5(L)条的规定,如果被告想援引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免责抗辩,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原告必须参与了该娱乐活动,该娱乐活动还存在重大受伤风险;第二,原告所受的伤害是由危险性娱乐活动中的“显著风险”(obvious risk)实际发生所致。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必须弄清以下三个概念:“娱乐活动”、“重大受伤风险”和“显著风险”。
(一)娱乐活动(recreational activity)
根据该法第5(K)条的规定,“娱乐活动”包括:(a)任何体育活动(无论该体育活动是否为有组织的);(b)任何以愉悦、放松以及休闲为目的的活动;(c)在特定场所(如海滩、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观赏或参与体育活动或以愉悦、放松以及休闲为目的的活动。[7]
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娱乐活动”的范围非常宽泛,包括一切娱乐休闲活动。但从澳大利亚的习惯称法以及最新修订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产业分类体系”(ANZSIC)来看,“recreational activity”特指以体育运动形式开展的休闲活动或娱乐活动。根据ANZSIC中的分类,编号为91的“体育与娱乐活动”下设“体育与体育娱乐活动”类别;而“体育与体育娱乐活动”又包括体育运动竞赛表演和以体育运动项目为核心开展的娱乐活动。[8]从立法的界定来看,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中的“娱乐活动”即相当于“体育娱乐活动”,它必须同时具备“休闲性”和“运动性”两种属性。
根据该法第5(K)条的规定,任何以休闲为目的的体育及相关活动都可以视为本条款中的娱乐活动,包括有组织的业余体育比赛。那么,职业体育比赛是否属于这里所讲的“娱乐活动”呢?实际上,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并不等于职业体育活动,该条款的适用范围应该排除职业的或非休闲性的体育比赛。[9]
(二)重大受伤风险(a significant risk of physical harm)
第5(K)条规定,“‘危险性娱乐活动’指存在重大受伤风险的娱乐活动”。因此,娱乐活动的“危险性”取决于该活动中的重大受伤风险。
1.风险与损害
重大受伤风险既涉及风险(risk),又涉及人身损害(physical harm)。但“重大”是限定风险的几率还是损害的程度,立法并没有明确说明。如果仅从字面含义和通常的语法习惯来看,“重大受伤风险”中的“重大”似乎是用来限定“风险”而不是“损害”的,因此将“重大受伤风险”解释为“重大风险”似乎更为合适。[10]
但现实中“风险”与“损害”并不总是均衡的,有时候风险很高但损害很轻微,有时候损害很严重但风险很低。只考虑风险发生的几率,而不考虑损害的严重程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风险的发生几率以及损害的严重程度,最终都会影响到对危险性的判断。笔者认为,本条款中重大受伤风险的成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潜在的损害必须很严重。不管该损害实际发生的几率有多大,潜在损害的程度必须是很严重的。如果潜在的损害并不严重,即使风险发生的几率很高,该风险也不会被认为是“重大风险”。
第二,风险发生的几率不能太低,必须有一定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其标准“介于微乎其微的风险”和“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之间。也就说,风险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只要大于“微乎其微”的程度即可。而且相应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客观的,比如,可以以特定活动中有关事故的发生率为依据来判断风险发生的几率有多大。
2.其他因素对重大受伤风险的影响
风险与损害都是抽象的概念,在具体判断时,还需要结合个案中的特定行为、特定场景以及参与者的主观因素(如年龄、经验及理性等)来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娱体活动中的风险,不仅来源于活动本身。很多其他因素,如开展活动时的场地环境、受害者自我保护能力等也可能诱发危险。时间、地点、行为能力、年龄、理性、活动设施甚至天气都可能让没有风险的娱体活动变得危险起来。此外,受害者以及侵害人的专业程度和经验对危险性认定的影响也值得考虑。比如,某项运动对训练有素的参加者并没有危险性,对一个刚入门的新手却可能具有风险。因此,尽管“重大受伤风险”也应当遵循一般合理人的标准,但这个一般合理人应当是在包括当事人专业程度及经验在内的特定情况下来假定的。
这种综合性考量方法最早由Basten法官(Basten J. A.)在2006年的Fallas案中提出来。Basten法官认为,在分析重大受伤风险时,应认真探究该行为发生时的特定场景和参与者的主观因素(如年龄、经验及理性等),并确定对于符合所有这些因素要求的一般合理人来说,重大受伤风险是否会发生。[11]这种考量方法在该案中得到了另一位法官Tobias(Tobias J.A.)先生的赞同,并在之后的Jaber案中得到遵循。[12]但笔者认为,该方法的缺陷在于:由于需要根据特定案件事实及个案的具体情况来作判断,法官具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对该司法裁量权不加任何限制,法官的任意适用会让“危险性”的认定变得飘忽不定。
(三)显著风险(obvious risk)
2002年《民事侵权法》第5(L)条规定:“危险娱乐活动中的显著风险致害免责:(1)被告对于原告在参加危险性娱乐活动时,因该活动中显著风险实际发生所导致的人身伤害,不承担过失责任;(2)不论原告是否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本条都适用。”[13]
该法第5(F)条规定:“(1)根据本条款的目的,“显著风险”指对在当事人所面临特定情况下的“一般合理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风险。(2)显著风险包括容易觉察的风险和常识性的风险。(3)风险并不会因其发生概率很低,而不能构成显著风险。(4)显著风险并不一定是突出的、显眼的或者有形的。”[14]
确定原告所参加的活动为危险性娱乐活动后,下一步就是要确定原告所受的伤害是由显著风险的实际发生所致。
1.可预见性
如果实际发生的风险无法被预见,它就不可能成为显著风险。风险可以被预见,意味着原告在参与该危险性娱乐活动时即已认识到风险。正因如此,原告应该对他们选择面对该风险的后果负责。至于对风险预见的程度,根据第5(G)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风险的认识,是指当事人认识到该类型的风险,而不要求当事人认识到风险的准确性质、程度或者其发生的方式”。[15]
关于显著风险的可预见性,结合法官在判例中的解释,应注意两个问题。
(1)显著风险必须与危险性娱乐活动有关联性
在上述Fallas案中,上诉审法官认为实际发生的显著风险应该与被界定的危险性娱乐活动有关。因为只有在危险性娱乐活动中发生的或者与该活动有关的风险才可能被当事人所预见。笔者认为,关联性要求在原告的自担风险与被告的过失责任之间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因为危险性娱乐活动以外的风险常常是因被告违反其注意义务而引起,如果不作此限定,该条款会被滥用于危险性娱乐活动以外的情形,从而对原告造成重大不公。
(2)显著风险不包括被告的重大过失
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是对过失责任的免除,它隐含了这样一个疑问:被告的过失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显著风险?有学者认为过失并不是原告应该预期的风险。[16]但根据第5(L)条,显著风险是包括了过失行为致害的风险的。Ipp法官认为:“没有过失就没有诉因和侵权责任,立法会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不可避免要接受对方过失的风险,这与立法目的是一致的。”[17]如果显著风险排除被告过失造成的风险,显著风险与第5(I)条中的固有风险几乎无异,该条款的设置就成了多余。但重大过失不在可预见的风险范围内。
2.一般合理人标准
根据第5(F)条规定,显著风险的认定取决于该风险对于一位处在受害者位置的一般合理人(reasonable person)来说是否显而易见。第5(L)条也规定,“不论原告是否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本条都适用一般合理人标准”。这实际上是对显著风险认定标准的客观性要求。一般合理人是指具备普通人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的普通人。[18]“处在受害者的位置”应该同时符合时间和空间上的条件:在原告遭受损害的特定时刻和特定环境下,实际发生的风险对于假定的一般合理人而言是否具有“显著性”。
但“处在受害者的位置”也可以被宽泛理解为包括年龄、心智成熟度以及个人经验等无法复制的个体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因素可能对“显著风险”的判断造成影响,一般合理人标准的适用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用与受害者年龄、心智等特征相当的一般合理人标准。[19]
3.显著风险与重大受伤风险
Basten法官在Fallas案中分析显著风险与危险性娱乐活动的关联性时,试图进一步推断显著风险必须也是实际发生的重大受伤风险。他认为,危险性娱乐活动中至少存在一个重大受伤风险,并且该重大风险最终实际发生并导致原告受伤,该重大风险必须满足第5(F)条显著风险的规定。但这一观点遭到了Ipp法官的有力反驳。[20]
重大受伤风险使娱乐活动变成了危险性娱乐活动,但实际发生的显著风险不一定是重大受伤风险。立法中也没有出现“显著且重大风险”的表述。重大受伤风险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而显著风险是已经实际发生的。在重大风险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显著风险的情况下,第5(L)条也可能适用。Ipp法官对此进行了例证:板球运动因涉及几种重大受伤风险而具备危险性娱乐活动的性质,比如“捕手”被“投球手”的球板所击伤就是比较常见的重大受伤风险。实际比赛中,如果在“死球”情况下,一名粗心的外野手将球扔给捕手,因捕手未觉察而被砸伤。这种情况下的风险由于发生的几率很低而难以构成重大受伤风险,但它却是一种显著风险-第5(F)条第3款明确规定,即使风险发生的几率很低,也有可能构成显著风险。因此,如果受伤的捕手起诉这名外野手,即使其伤害是由非重大受伤风险实际发生所致,但只要被告能证明娱乐活动为危险性娱乐活动,也能证明其受伤是由显著风险所致,被告就能援引第5(L)条进行抗辩。[21]
三、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适用-与判例法的结合
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整个英美法系都无先例,加上立法技术不成熟,该条款的概念表述多有抽象模糊之处。这给该条款的适用带来了麻烦,因此它不得不依赖于判例法的解释和限制。法官也因此在该条款的适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Ipp法官,他不仅是2002年侵权法改革中“IPP委员会”的主持者,也是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的法官。在2002年《民事责任法》颁布后,他在多起危险性娱乐活动侵权案件的上诉审中担任重要角色,对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为法官们在不同案件中对该条款中存在争议的表述不断进行辨析,危险性娱乐条款才在立法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明确。而且,由于法官们的谨慎解释,该条款并没有像人们先前质疑的那样被滥用;相反,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他们通过判例法作出了很多限制。这些判例形成的解释在后来的案例中逐渐得到遵循。判例法中形成的原则与2002年《民事责任法》的相关条款一起,构成了危险性娱乐活动免责制度的完整内容。
以下三个案件对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适用及其判例法解释具有重要影响。
(一)Fallas案[22]
原告(Mourlas)和被告(Fallas)约了两位好友驾车去树林里打猎。由于是晚上,必须利用车灯来提供照明,因此安排原告在车内控制车灯,其他几位则携枪下车搜寻猎物。中途被告准备回车上,原告提醒被告不要带着有子弹的枪上车,被告则不断向他保证没事。上车后被告感觉枪口被卡住,开始不停地摆弄手枪,这时原告再次提醒被告“去外面折腾”。但被告没下车,最后不小心触动手枪机关,子弹击中原告大腿,导致严重受伤。原告起诉被告,被告根据2002年《民事责任法》第5(L)条提出抗辩。初审法院认为,由于原告当时只是坐在车内,并未实际参与猎捕活动,本案不符合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规定,因此被告应承担过失责任。被告不服并上诉。
Fallas案是使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第一次得到全面适用的案例,该案三位法官的判决意见对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中的几个重要概念作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辨析,他们的一些分析思路和结论也被之后的判例广为遵循。
在本案中,被子弹误伤的风险在打猎活动中并不罕见,尤其夜间打猎时,风险会更大,被子弹击中的人身伤害也会很严重。因此,仅从风险的几率与损害的严重程度来看,夜间打猎行为显然存在重大受伤风险。但具体到原告受伤时的特定场景,当时是否存在重大受伤风险值得探讨。首先,对本案中的夜间打猎活动来说,利用车灯提供照明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不能因为原告未下车持枪打猎就认为其行为与该活动无关,原告在车内为打猎提供照明的行为应被视为参与了夜间打猎这一娱乐活动。但原告这种“有限参与打猎”的行为与其他人持枪打猎的行为毕竟不同。在这里,三位上诉审法官对于原告的特定行为是否存在重大受伤风险存在分歧。Ipp法官认为,在该案的具体场景中,原告在车内提供照明的行为隐含了一个前提:某个粗心的同伴随时会将有子弹的枪带回车上,从而导致车内的人被击中受伤;Tobias法官也认为,因受到参与者对打猎缺乏经验、过于兴奋及冒险心理等因素影响,在本案中被子弹误伤的重大风险是存在的;Basten法官却认为,尽管原告参与了打猎活动,具体到原告当时在车内的特定行为,并不存在重大受伤风险。最终上诉审采用多数意见,认定原告的行为符合危险性娱乐活动的条件。
接下来是对显著风险的认定。打猎活动中被子弹误伤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该风险更准确地来说是指以猎物为目标时被子弹误伤的风险。在车内被子弹误伤的风险与在打猎中被枪支误伤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前者与打猎活动的关联性已经很弱,尤其当原告坐在车内且被告不断保证说“没事”的情况下,原告很难预见到这种风险。因此在车内被子弹误伤的风险并不构成危险性娱乐活动的显著风险。Basten法官认为,原告在车内被子弹误伤的风险既没有可预见性,与危险性娱乐活动也没有关联性(当然,如上所述,他原本就否认原告的活动属于危险性娱乐活动)。因此,原告被子弹误伤并不是显著风险实际发生所致。
但Ipp法官认为显著风险不成立的理由是被告存在重大过失。在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不要将有子弹的枪带上车的情况下,被告一再保证没事,他的固执己见导致其未能采取措施避免事故。本案的被告过失已经超出了一般疏忽的范围,被告的态度和行为均显示其具有不负责任的重大过失。因此原告因被告偏执行为导致受伤的风险不构成第5(F)条中的显著风险。
最终,本案上诉判决认为原告被子弹误伤的风险并不是显著风险实际发生所致,其与初审判决的理由虽不一致,结论却相同。因此,上诉审维持了初审判决。
(二)Falvo案[23]
原告Falvo在参加一场由澳大利亚带式榄球协会和Millers Reserve体育场共同主办的带式榄球(非撞式榄球)[24]比赛时受伤。Millers Reserve的草坪之前存在多处破损。赛前,体育场用沙子将这些破损处填补起来,但填补处与旁边的草皮相比,仍有些许的凹凸不平。比赛中原告跑到一处草皮覆盖的沙坑时,由于沙地较软,原告脚底突然失去控制,重重摔了一跤,导致膝盖受伤。原告之后对澳大利亚带式榄球协会和体育场提起过失之诉。初审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依据2002年《民事责任法》中的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认为原告应自己承担带式榄球比赛中的受伤风险。因此被告对原告所受伤害不承担过失责任。原告不服并上诉。
上诉法院认为,带式榄球与联盟式橄榄球不同,它没有抱截动作,几乎不存在受伤的风险。而联盟式橄榄球由于经常出现受伤事故,一般情况下都被视为危险性娱乐活动。相比之下,带式榄球本身并不存在重大受伤风险。上诉法院的Ipp法官认为原告参与的井不是危险性娱乐活动,不能适用该条款的免责抗辩。最终上诉审推翻了初审判决。本案相对简单,对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的贡献主要是Ipp法官在该案中确定了重大受伤风险中“风险”与“损害”的关系。
(三)Dederer案[25]
原告Dederer是一个14岁半的男孩,某个假日在一座桥上玩跳水。当时原告从桥上看河水呈深绿色,似乎深不见底,在前两次跳水都没有冲到河底的情况下,他第三次跃入水中,在俯冲过程中却撞到沙洲并严重受伤。原告跳水的这座桥多年以来一直被当地人当成跳水场所,而且在原告受伤当天也有另外一群小孩在这里玩跳水。当地政府一直试图阻止人们这种危险的行为,但屡屡无效。直到1993年,政府在桥上挂出了“禁止跳水”的标志,但并没有提示河道的深浅度。
初审法院认为,虽然跳水是“危险性娱乐活动”,但原告无法从该危险性娱乐活动的“显著风险”中预料到其所受伤害。“禁止跳水”的标志没有注明河水的深度,而以原告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根据当时河水颜色的视觉效果,他无法预料到人水后会撞到河底浅滩并造成身体严重受伤。初审法官认为,以原告的年纪和经验,本案中受伤的风险对他而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被告不能援引第5(L)条中的“显著风险”来免除自己的过失责任。[26]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Ipp法官是上诉审法官,他认为初审法院根据原告的主观认知来判断风险的“显著性”问题是错误的,正确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处在原告位置的一般合理人”。根据2002年《民事责任法》第5(G)条,只要原告认识到了致害风险的类型,该风险就属于“显著风险”。即使原告不了解该风险的准确性质、致害的程度和风险实现的方式,也不影响“显著风险”的成立。尽管被告标识的“禁止跳水”没有具体说明风险会如何产生,但标识本身足以让一个14岁半的一般合理人认识到跳水的危险。因此,上诉审判决“显著风险”成立,被告可以援引第5(L)条规定的豁免。
四、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与以前举国支持竞技体育的发展相比,国家开始更为重视大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在休闲和健身方面的观念也逐渐加强,休闲体育产业在经济逐渐强大的中国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另一方面,我国体育产业正在经历从“举国体制”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阶段,目前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健身的需求,休闲体育产业必将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27]因此当前体育产业的发展利益以及体育产业业主市场身份的确立,都会对体育活动中过失伤害责任的归责产生影响。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休闲体育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过失体育伤害的归责制度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我国目前在过失体育伤害归责制度方面与澳大利亚还存在一些差距。
其一,保险介入的程度大相径庭。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商业保险在体育产业中就已构筑了一套完善的救济体系,不管是职业运动员,还是休闲体育活动的参加者,在体育活动中受伤后都可以获得足够的保险赔偿。在“保险危机”爆发后,为了保持侵权法的独立性,同时基于保护体育产业发展的考虑,立法对休闲体育中的过失伤害责任进行了明确限制。但在我国,责任保险在体育领域不是过分介入,而是介入不足。国际体育界早已针对运动员开辟了专业而多样化的险种,而我国的专业性体育保险还处于探索阶段。这种状况导致在比赛或训练中受伤甚至落下职业病的运动员在疗养中和退役后得不到足够保障。[28]这一方面是因中国的商业保险在专业性体育保险领域缺位所致,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当“举国体制”下的体育逐渐走向市场化时,体制与市场的顺利对接尚未能实现,相关保障还很难以健全的方式及时跟上。具体到休闲体育领域,由于相关的责任保险也没有在该领域得到广泛适用,被告在经营休闲体育产业时往往会背负过于沉重的潜在赔偿负担。保险是分散体育伤害风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途径,我国体育产业应该培育相应的保险市场,让商业保险充分介入体育伤害风险的管理。但同时应警惕对保险的过分依赖,以保持侵权法自身的独立性。
其二,我国现行立法对体育活动中的过失责任并无明确规定。与英美法中限制娱体活动中过失致害责任的趋势相比,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都没有细致地考虑体育活动的特殊性,这一领域的过失责任归责仍遵循传统的安全保障义务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甚至在有关案例中适用民法上的“危险责任”来追究体育场所经营者或管理者的过失致害责任。[29]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也只是笼统地将安全保障义务适用于娱乐活动,并没有考虑到体育活动中人身伤害的特殊性。如果娱体场所的经营与管理者对原告参与危险性娱体活动所受的伤害也要承担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甚至“危险责任”,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保险救济不足,必然会给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因此,我国应考虑体育产业发展的需要,对体育活动中固有风险及显著风险引发的责任分配,作出符合社会现实的规定。立法者可以在未来的侵权法司法解释中借鉴澳大利亚侵权法中的“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对体育活动中的过失致害责任给予一定的限制或豁免。但同时应该限定具体的适用条件,防止该条款被滥用而反过来挫伤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这个“度”的良好把握,要求立法者深入调研我国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需求,在不违背侵权责任分配的正义原则基础上,结合保险的介入程度,作出合理的平衡。此外,也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遴选有关过失体育伤害归责的指导性案例,为数量日益增加的过失体育伤害案件提供统一指导。
【注释】
[1]NSW Supreme Court, Tort Law Reform in Australia, available at ,retrieved Oct. 12,2011.
[2]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的著名法官David Ipp是该专家委员会的主持者,委员会因此取名为“IPP委员会”。
[3]Wikipedia, The IPP Report.,available at , retrieved Oct. 20,2011.
[4]Peter Cane, Reforming Tort Law in Australia: A Personal Perspective,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27,2003,p. 649.
[5]Barbara McDonald, The Impact of the Civil Liability Legislation on Fundamental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Com-mon Law of Negligence, Torts Law Journal, Vol. 14, 2006,pp.22-54.
[6]Civil Liability Amendmen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ct 2002, available at retrieved Nov. 18,2011.
[7]Section 5K of the Civil Liability Act 2002 (NSW)。
[8]Se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292. 0-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ANZSIC) , 2006(Revision 1. 0), available at retrieved Nov. 18.2011.
[9]作出该判断的另一个依据:按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产业分类体系(ANZSIC),门类“体育与体育娱乐活动”(Sports and Physical Recreation Activities)由体育运动竞赛表演和以体育运动项目为核心开展的娱乐活动两大类组成。因此,职业体育应该属于Sports,具有休闲性质的“体育娱乐活动”(Sports and Recreation Activities)才是本文所指的“娱乐活动”。
[10]Deborah Healey, Sports and the Law, 4th ed.,Sedney: UNSW Press, 2009, p. 141.
[11]Fallas v Mourlas [2006] NSWCA 32.
[12]Jaber v Rockdale City Council[2008] NSWCA 98.
[13]Section 5L of the Civil Liability Act 2002 (NSW) .
[14]Section 5F of the Civil Liability Act 2002 (NSW)。
[15]Section 5G of the Civil Liability Act 2002 (NSW)。
[16]Barbara McDonald, The Impact of the Civil Liability Legislation on Fundamental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Com mon Law of Negligence, Torts Law Journal, Vol. 14, 2006, pp.22-54.
[17]Fallas v Mourlas [2006] NSWCA 32.
[18]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19]David Thorpe, Sports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 147.
[20]Fallas v Mourlas [2006] NSWCA 32.
[21]Fallas v Mourlas [2006] NSWCA 32.
[22]Fallas v Mourlas [2006] NSWCA 32
[23]Fallas v Mourlas [2006] NSWCA 32.
[24]带式榄球(非撞式榄球)是一种联盟式橄榄球的衍生运动,以拿走对方带在腰上的魔术贴以表示抱截。当对方拿走其魔术贴时,需要大声地说“TAG”以令被抱截者知道要传球给后面的人。这个运动没有任何年龄、性别的限制。它的危险度亦比联盟式橄榄球低,这是因为没有抱截的动作,并不会令他人受伤。
[25]Roads&Traffic Authority of NSW v Dederer&Anor [2006] NSWCA 101.
[26]Roads&Traffic Authority of NSW v Dederer&Anor [2006] NSWCA 101.
[27]参见曹辛:《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载《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第E31版;吕明合:《陈培德:“群众体育才该搞举国体制”》,载《南方周末》2010年12月30日第7版。
[28]参见麦卡:《中国体坛站上“断裂带”》,载《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2期。
[29]“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民事判决95年度诉字第1016号”。
- 认准易品期刊网
1、最快当天审稿 最快30天出刊
易品期刊网合作杂志社多达400家,独家内部绿色通道帮您快速发表(部分刊物可加急)! 合作期刊列表
2、100%推荐正刊 职称评审保证可用
易品期刊网所推荐刊物均为正刊,绝不推荐假刊、增刊、副刊。刊物可用于职称评审! 如何鉴别真伪期刊?
都是国家承认、正规、合法、双刊号期刊,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 可查询,并全文收录。
3、八年超过1万成功案例
易品期刊网站专业从事论文发表服务8年,超过1万的成功案例! 更多成功案例
4、发表不成功100%全额退款保证
易品期刊网的成功录用率在业内一直遥遥领先,对于核心期刊的审稿严格,若未能发表,全额退款! 查看退款证明

- 推荐
- 点击
- 浅谈基于《企业内部控 03-14
- 基于多元主体参建的西 01-22
- 我国双语播音专业办学 01-30
- 打造国际品质 选择国 08-08
- 怎样加强企业思想政治 02-29
- 试论我国家族企业的产 07-13
- 企业管理论文范文:要 07-16
- 中小企业现金流量管理 01-14
- 浅析文化事业单位财务 07-09
- 电视编辑工作思维探析 07-30